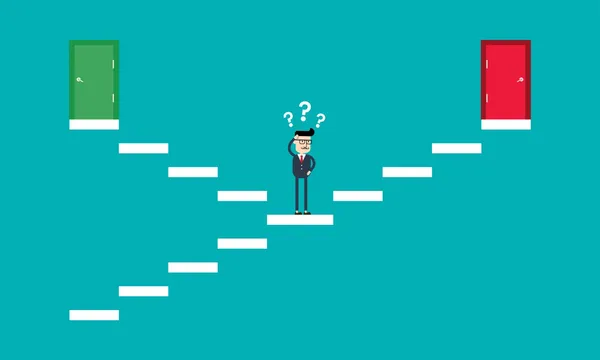人類進行決策時會有缺失與弱點,而認知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埃姆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就是揭開此缺失與弱點最強而有力的其中二位代表。他們兩人的研究已為現在所熟知的行為經濟學奠定了基礎。為了表彰他們的成就,卡尼曼於2002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特沃斯基於1996年時已逝)。 他們所提出的首批認知偏見中的一項,證實了提問的方式(也就是問題被「框架」的方式)會影響問題的答案。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在他們其中一個經典框架研究中,讓受測者觀看一段特殊疾病爆發的影片,這場疾病預估會造成600人死亡。他們給受測者2個對抗疾病爆發的方案,請受測者從中選一:
- 如果採用計畫A,可保全200人的性命。
- 如果採用計畫B,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以救活所有人,但有三分之二的機率會造成全部人死亡。
換句話說,就是要在「200人被拯救這個確定結果」與「全部人死亡還是活命這個不確定結果」間進行選擇。(這裡要注意,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計畫B,平均下來能救活的人數也是200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對錯,只是面對可怕情況採行不同方式罷了。
他們發現在此研究中,有72%的受測者選擇保證救活200人的選項(計畫A),而有28%的人選項賭一把,希望能拯救所有人。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卡尼曼與特沃斯基讓另一群受測者觀看相同的選項,只是以不同的文字來描述選項。
- 如果採用計畫A,會造成400人死亡。
- 如果採用計畫B,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以救活所有人,但有三分之二的機率會造成全部600人的死亡。
第二部分研究中的選項A與B都同於第一部分研究,唯一不同處就是用字上的差異。可是,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卻發現在第二部分研究中,人們的決定全然相反,大部分受測者(78%)選擇B,這與第一部分中只有28%的人選擇B的情況截然不同。換句話說,以「600人中會有400人死亡」框架起的選項,比起「600人中會有200人存活」的框架選擇,更容易促使人們去採納那個像是場賭博的選項;「一定可以拯救33%的人」是人們可接受的情況,但「必定會造成67%的人死亡」,則是我們所不能承擔的後果。
保留?失去?用字不同的選擇決策
框架效應已經被重複實驗了許多次,其中還包括在實驗進行時同時對受測者進行大腦掃描的研究。有篇框架研究包含了多回合的投機判斷,每一次實驗開始時都會先讓受測者拿到一筆錢。舉例來說,在第一回合中,受測者會拿到50美金,並被要求在下二個選項中做出選擇:
- 保有30美金。
- 賭一把,有一半的機率可以保住全部50美金,但也有一半的機率失去全部的錢。
受測者並沒有真的拿到這筆錢,所以事實上也非真的持有或失去,不過他們有強烈動機想要表現出色,因為領到的車馬費是以贏錢的比例做為依據。給予受測者上述二個選項後,在 43%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賭一把(選項一)。接著再把選項一的用字修改,並給同一批受測者進行選擇。新的選項如下:
- 失去20美金。
- 賭一把,有一半的機率可以保住全部50美金,但也有一半的機率失去全部的錢。
當選項一框上了「失去」這個框架時,人們選擇賭一把的情況增為62%。雖然保有50元中的30元與失去其中的20元是一模一樣的意思,但用「失去」來框定問題讓可能失去整整50元的風險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20位實驗受測者中,當選項是以「失去」來陳述時,每一位都曾決定要多賭點。明顯地,任何一位宣稱自己的決定是立基於理性分析的受測者,可是大錯特錯了。
雖然與「保有」框架選項相比,所有受測者在「失去」框架的選項中都有多賭點的情況出現,但這其中還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個別差異: 有些人在選項一以「失去」為框架時,賭賭看的情況只會多一些,但有些人卻是大賭特賭。 我們可以說,在「失去」框架中只多賭一點的人較具理性,因為問題的用字對於他們的決定只有輕微影響。有趣的是,受測者「理性」的程度與他們前額皮質區(也就是眼眶額葉皮質)的活動量具有相關性。這與一般認為大腦前額區域在進行理性決斷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一致。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的另一篇研究顯示,在二種治療方式中,醫生該建議病人採用哪一個治療方式,會因此位醫生是否已被告知其中某種方式僅有10%的存活率或90%的死亡率,而影響其判斷。
在卡尼曼與特沃斯基進行研究之前,多數商人就已深知框架的重要性。所有廠商一直都知道,必須以本公司產品價格比其他公司產品便宜10%,而非僅為其他公司產品90%的方式來打廣告。同樣地,某個廠商也許會宣稱自家產品為「少了50%卡路里的低脂巧克力糖霜球」,但他們絕不會以「仍有50%卡路里的低脂巧克力糖霜球」的說法來行銷。在某些國家,顧客若以信用卡消費,會比以現金付費多付一些手續費(因為信用卡公司通常會抽走1%~3%的購物金額)。但信用卡與現金的金額差異,總是被框架成付現有打折的模樣,而不是信用卡外加手續費的實際情況。
拜登與布萊德彼特年齡為何?題目順序影響錨定現象
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在另一個經典的實驗中,描述了另一種認知偏見: 錨定現象 。他們在這篇研究中請受測者想一想,非洲國家在聯合國中所佔百分比是否高於或低於某一特定值:其中一個受測組所給定的值為10%,另一組則為65%。(實驗者讓受測者相信這些數字是隨機取樣得出)。接下來請受測者預估非洲國家在聯合國中所佔百分比為多少。10%與65%這二個數字的作用就是「錨定」,實驗結果顯示這會影響受測者的估計值。在錨定數值低(10%)的那一組中,平均估計值為 25%,而錨定數值高(65%)的那一組所估算出來的平均值竟高達45%。 錨定偏見呈現出「人們對數字的估算會受到無關數字影響」的情況。
坦白說,一直以來我總是有些懷疑,像錨定作用這樣的認知偏見到底有多強大,所以我自己進行了一個非正式的實驗。我對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問了2個問題:
(一)你覺得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的年紀多大?
(二)你覺得演員布萊德彼特(Brad Pitt)現在幾歲?
每次詢問時我都會對調問題的次序。所以我就有了順序不同的二組:一組是先問總統拜登的年紀,再問布萊德彼特(拜登/布萊德彼特組);另一組則是先問布萊德彼特的歲數,然後再問總統拜登(布萊德彼特/拜登組)。
我最先感受到的驚人發現是,自己認識的人竟然有50個之多。後續進行統計後我有了第二個發現,布萊德彼特/拜登組的年紀平均預估值為布萊得彼特42.9歲、拜登61.1歲;而在拜登/布萊德彼特組中,則是布萊德彼特44.2歲、拜登64.7歲(布萊德彼特於實驗當時的年紀為45歲,而拜登為66歲。)先以布萊德彼特的年紀「錨定」後,對於拜登年紀的估算明顯較低。
而以拜登的歲數錨定後,對布萊德彼特年紀的估算則較高;不過這個差異在統計上並沒有意義。當人們需要進行猜測估算時,錨定作用才會出現,若是詢問美國人美國共有幾州這種答案確定的問題,無論用什麼來錨定,都不會有效果。看起來布萊德彼特對於拜登歲數估計的影響,比起拜登對於布萊德彼特年紀的影響可能要來得大,因為人們對布萊德彼的年紀估計較接近實際情況(取樣的區域是我自己的居住地洛杉磯)。
估算拜登年紀時因布萊德彼特歲數所產生的誤導,對現實生活似乎沒什麼影響。不過在其他情況中,錨定作用則是一個非常容易被利用的方式。我們都聽過有些人士對大公司提告所求償的天文數字—最近一個案例是陪審團認定一家香煙公司要賠償一位人士3億美元的案件。這些天文數字不單單是因為陪審團對數字0的模糊認識所造成,也代表著一種藉由訴訟產生錨定效應的合理策略,也就是在審理過程中將大筆數值深植陪審團心中。同樣地,在進行薪資協商時,錨定效應似乎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當雙方都不清楚此職位的薪資價值時。一旦其中一方開始提出一個薪資價碼時,它就可能成為雙方所有後續討價還價的錨定了。
無所不在的日常偏見,來自生活事件的脈絡
框架偏見與錨定偏見的特點都是「先前事件會影響後續決定」 ,所謂的先前事件像是一個問題的用字或是某個給定的數字等等。從演化的觀點來看,因為語言與數字本身都是新產物,這些特定偏見顯然是最近才現身的。但框架與錨定現象不過就是極其一般的現象,也就是事件的脈絡會對後續發展造成影響而已。
如果人類不是「以事件脈絡為依據」的生物,那麼就什麼都不是了,而語言則是我們取得事件脈絡的眾多資源之一。一個音節的「意思」部分是根據出現在它前面的音節是什麼來決定(如today/yesterday;belay/delay)。一個字的意思也常由出現在它前面的字眼來決定(如床蝨臭蟲/電腦臭蟲;大狗/熱狗)。而一段話的意思會因說話者與場所的不同而受到影響(「He fell off the wagon」這句話的意思會因你所在地點而所有不同,若在遊樂場聽到則是「他從車上掉下來」的意思,但在酒吧中,就成了「舊癮重發」之意了)。如果不小心割傷手,你的反應會因獨自在家或是在商務會議中而有所不同。如果有人說你是怪人,你的反應也會因這人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上司還是陌生人而有所不同。所以事件的脈絡才是關鍵。
我們會因為一個選項被框架為「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存活」或「有三分之二人會死亡」而受到影響,這是件非常不理性的事情。但這種可互換的說詞代表的卻是不同的意見。在多數情況下,人們的用字遣詞並非恣意獨斷,而是刻意用來表達事情的脈絡以及提供額外的溝通管道。如果兩個選項分別為「三分之一的人能存活」以及「三分之二的人會死亡」,也許發問者正在給我們第一個選項比較好的暗示。
的確,我們都在不自覺地情況下自主地使用了框架效應。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面對十分震驚的兄弟姐妹時,會以「爸爸有50%的機率會死」而非「爸爸有50%的機率會存活」來轉述緊急手術的預期結果嗎?雖然多數人不會刻意思考要如何框架問題與自己的說法,但我們直覺地就會抓到框架的要點。就連小孩也知道,在爸爸問他們是否吃完自己那份蔬菜時,最好以「我幾乎把蔬菜吃光光了」而非「我還留了一些蔬菜在碗中」這樣的框架來回答。 框架與錨定偏見不過就是,我們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最好不要那麼敏感的例子罷了。
本文授權轉載自《大腦有問題?!──大腦瑕疵如何影響你我的生活》,Brian Clegg著,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蘇柔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