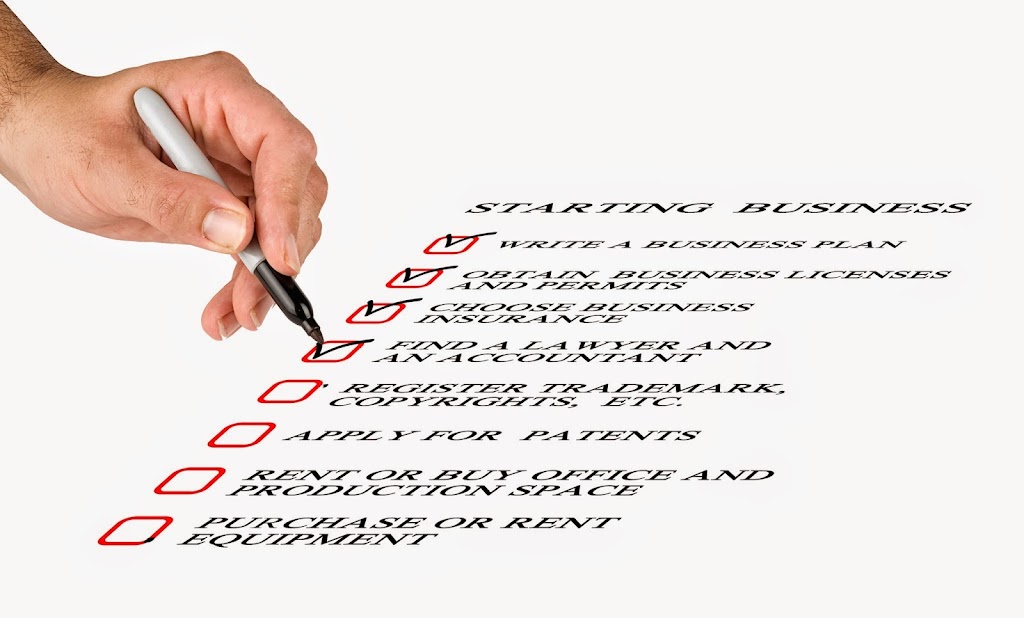Q:你那時候怎麼會進入網際網路這個世界,有什麼特別的因緣嗎?
A:主要的因緣還是在通訊。以前在美國UCLA讀書,老實講,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圖書館,老師有多厲害其實我倒不覺得,美國老師也有人很混的,但是他們的圖書館系統,方便得實在讓人不得不佩服他們投入的工夫。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它可以讓你透過Telnet(遠端登錄系統)在家裡查,所以我回到台灣以後,還常會去查學校的資料。但是你查了以後,就必須把書的資料記起來或印下來,寫信或傳真請美國朋友幫你印書的內容,再寄回來。
到了九三年夏天,我的partner蕭景燈回來(以前我們住在一起),看我還在電腦上用Telnet,就說:「你怎麼這麼沒效率?現在有個新東西叫Gopher。」其實,在那之前台灣也有人在玩Gopher,Gopher可以看到文字模式,它和現在World Wide Web有點像,只是它只能看純文字而已,但全文可以看到,可以下載,還可以印,那時就覺得真方便。
到十一月的時候,蕭仔(蕭景燈)又跟我說,可以看到圖了,我們下意識地覺得這個媒體好厲害,就開始去接觸。
我過去對台灣的媒體監督滿有興趣,這其實是來自對民主化過程的一種不同思考。我覺得到九○年以後,台灣進步的最關鍵因素應該是媒體,因為媒體是一個經常性的監督機制,民主政治能做的制度改革已經到了一個程度,接下來大家要不要照這個規則來玩,那需要整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要透過日常生活的教育,媒體在裡面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其實,這跟我在九○年初做過的一個媒體監督的研究有關係,也跟我長期關注社會運動有關,因為過去的社會運動團體和現在不一樣,社會運動的議題和人,在媒體裡面基本上都是被忽略的,今天講教育,現在有人會去訪問人本基金會,以前是遊行幾萬人走完後,媒體將任何人都訪問了,就是沒有去訪問遊行的人,這個都可以調錄影帶出來看。
過去我們所關心的東西,在媒體裡面大量被忽視,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因為社會運動所關注的是新的理念或理想的提出,那對社會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教育和衝擊,過去都被傳統媒體忽略掉了,談到的可能都是衝突的部分,可能是遊行或運動這個手段,而不是那些人為什麼會用這個手段去評論事情。
所以那時候接觸到Internet的第一個想法就是,網路是窮人的原子彈,一部伺服器就可以讓你暢所欲言。最早我們是這樣想的,所以就開始和我partner蕭仔(蕭景燈)做相關的研究。
到九四年的下半年後比較清楚,覺得網路以後應該是通訊及新社會大轉變的起頭,有點像當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一樣,看到的是一個很簡單的科學研究發現,但後面引發的改變很大。
我們在九四年底正式提出「蕃薯藤」這個概念,是因為「網路」外國人都稱它Web,網路的資料搜尋叫做Spider,蜘蛛和蜘蛛網在東方文化有負面價值,蜘蛛在西遊記裡都是壞蛋。我們想要用本土的名字去形容它,腦中一閃就是「蕃薯藤」,第一個原因是,它對在台灣成長的人很親切,蕃薯即使在很貧瘠的環境也可以生長,和網路一樣,網路不需要很皇家級的配備才能運作,只要你有一條電話線連通就可以。蕃薯藤它本身會蔓生,它會長出很多新的小蕃薯來,跟網路很像,網路連出去後會長出新的個體,而且新的可能會比舊的更多更大。
Q:你那時去美國是唸社會學博士班,為什麼沒唸完就回來?
A:我一直都讀社會學,博士班讀到一半,回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台灣社會環境在八○年底,九○年初的時候正好大變,心癢難耐,覺得一定要回來,那時看到Apple II、小教授和小博士,就想應該利用他們來整理台灣的資料。
在台灣唸研究所時,我算是台大社會系第一個論文做本土題材的,其他人都是寫馬克思、韋伯,我是拿社會學理去研究台灣的知識份子、《自由中國》和《文星》,還被嚴重警告,差一點就出事。
那時的挫折是想要了解過去的事實,卻發現找不到資料,所以看到電腦,跟幾個朋友就有一個最直覺的想法,應該建立一個台灣的資料庫,不必多作詮釋,只要把資料搜集來,讓大家有機會用自己的觀點去了解、詮釋它,甚至有衝突都沒有關係。
我八九年從美國休學回來,和幾個朋友成立一個叫無花果的機構,整理搜集台灣的資料。這個無花果的名字,就是吳濁流寫的小說名——《無花果》,其實也是師法吳濁流的意思,台灣人在不同時期都被不同的統治者壓迫,所以他們就跟無花果一樣,沒辦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開花,但時間到了還是會結出果子來,不會被消滅掉。那時單純地以為沒有問題,沒想到為了這件事被抓,說我們去找史明(旅居日本的台獨運動史學家),其實我們還找了很多其他人,很多人把台灣史料搶救到國外去,保存起來等以後再運回台灣,我們就找很多人說服他們把資料捐出來。
我們後來發現找到資料容易,但過去的資料都沒有數位檔,我們那時便開了一家也叫無花果的打字行,平常接一些外面的打字生意,公餘時間就彙整史料,後來那部電腦被調查局抱走,拿回來後不知道為什麼全都壞了。
Q:所以蕃薯藤剛開始的發展動機其實很單純,是奠基在資料的搜集?
A:對,一開始看到網路媒體,只知道它會是下一世代的媒體,最早的想法是透過網路來做原先在做的事情,可能會更快更方便,不用一個集中化的中心,成本更低,更有效,也更容易做到。
Q:從九四年到去年商業化之前,蕃薯藤都是一個非商業性的組織?
A:九五年底我們提出TeleCommunication(通訊)的概念,其實一部連在網路上的電腦不應該叫PC,應該叫TC,像送e-mail、和人家聊天、討論版,或抓取很多資訊,其實都是通訊的需求。到了九七年,就覺得講TC也不太對,因為TC可能不是一部連在網路上的電腦,太大、太不方便,以後可能有新的裝置。
在非營利的架構底下,我們把台灣文史資料盡量建到網站上,並說服公益團體,也把他們的東西放到網站上,這是有關內容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九五年後,我們成立開拓基金會,討論通訊相關法規的修訂;第三個部分才是大家最熟悉的搜尋引擎。
Q:參與運動的人都有一個過去的故事,為什麼你唸書時會去關心弱勢團體?
A:這可能跟從小個性有關係,我高中大學時有一陣子在教會出入,後來又去唸社會學,這是最主要的原因,社會學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支流,就是馬克思主義,它其實有很強烈的人文關懷,社會學的訓練會讓你對社會周遭的事情,採取介入關懷的態度。就好像宗教裡始終有出世與入世兩派,我是傾向入世的那種人。
Q:去年蕃薯藤作商業化的轉型,你自己怎麼調適應對這樣的轉變?這樣的經營模式會不會對你產生某種程度的衝擊?
A:其實這是很自然的過程,初期我們並沒有想到商業經營。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可以參與一個劇變的開始,有點像當年許多社會學大師在工業時代初期,覺得參與這麼大的一個時代運動這件事本身,就感到很滿足。
到了九七年底,就開始思考還需不需用一個資源有限的公益團體來苦撐,大部分人都在做義工,不計較到底有沒有薪水。對蕃薯藤來說,我們比較有興趣的不是一個business,而是一個參與industry的變化,我記得前後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討論要不要商業化,到九八年三月才達成共識;作為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團隊之一,勢必要引進新的資源,包括資金和人力。
我們現在的董事長——中研院院士孔先生(孔祥重)也是在這個背景下邀請來的,本來是不相識的,我們那時認為蕃薯藤有機會變成一個世界級的團隊,需要一個世界級的leader。那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向天借膽,就發了e-mail,說我們準備要轉成公司經營,需要幫忙,他竟然沒有回絕,他回e-mail說:「What can I help?」我又回了e-mail說:「我們缺一個董事長。」結果他還是沒有說No。
事實上孔先生也看到台灣的產業發展一定要軟硬通吃,因為前有強敵,後有追兵,靠硬體做到一個程度,後來只是在產製流程裡,賺管理效率的價差,毛利很小,那種生意做不長,參與蕃薯藤其實也就參與了台灣的軟體產業和網路產業,可以對台灣有貢獻,他也很快地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隊。
我覺得現在工作的節奏比較不一樣,商業的節奏要很穩定,我都喜歡用職業運動來比喻。蕃薯藤以前充其量只是一個運動的愛好者,現在像是職業運動裡的一支隊伍,比賽是比賽,訓練是訓練,隨時都要有它的節奏,不比賽時就得做重量訓練。國外很多的職業團隊看起來都是這樣,最後是要把節奏、style調出來,沒有說光打快攻或光打系統戰的那一種球隊一定會成功。
Q:蕃薯藤商業化後,身為執行長,你如何去面對股東對營利上的要求和壓力?
A:其實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從公益法人變成商業法人;心態上的調整,反而是對我和同仁一個較大的落差,調整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學。以前學習和工作是生命中兩個不同的階段,要學習完才能工作,而工作後就沒有學習的機會,但我想以後網路資訊時代的特性,就是學習和工作會變成同一件事情,網路時代變化快速,用過去的理解方式會有落差,而且不斷會有新的東西。現在大型世界級公司都有所調整,像IBM、HP和任天堂,每一年研發和教育費用都比台灣國科會預算多,都超過一億美金,讓員工伴隨公司也有自我成長。資訊網路時代最珍貴的資產是員工,每個人都要學,不因為你是公司高階主管,就有資格去教其他同仁,我覺得這是網路時代工作典範的改變,延伸到企業組織架構的改變。
Q:在這一次的大地震,蕃薯藤是反應最快的網站之一,當初你們怎麼樣應對突來的事件?
A:我們的網站是最早動起來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是做公益出身,很自然地就想到網路在這個事件裡,可發生很大的效用,另外是我們的社會責任,怎麼樣透過網站以線上募款等方式去幫助災區的人。第一個是把各種資訊趕快建上站來,第二個做社會心理重建等專業內容,我們甚至透過我們長期和學界的關係,編手冊和教材,這部分是傳統蕃薯藤的專長。我們也和世界衛生組織、日本神戶及美國加州方面聯繫上,把他們的地震手冊轉成中文,放在網站上給大家參考。另外是一開始便做英文版,希望讓國外的人知道,因為看來這個災害的規模會超過台灣獨自能夠承擔的,重建過程需要很多國外的幫助。
Q:外界認為商業化後的蕃薯藤步調比較慢,學術性與道德性也比較強,面對消費者不再具有優勢,你對這樣的觀察有什麼看法?
A:我覺得有些是價值上或判斷上的差異,比如說,蕃薯藤的節奏比較慢,我們反倒覺得是比較審慎,網路像是跑馬拉松,不是跑800公尺,我們一直在抓自己的配速。另一個判斷上的差異是,決戰點到底在那裡,我們認為現在其實言之過早,因為世界級、美國的主要成員都還沒進來,現在充其量也不過在打乙組的決賽,乙組決賽前兩名才可以升到甲組。我們希望自己是一個長期經營的團隊,目的不是上市或賣掉變現。
網路和其他傳統行業很像的是,要在最短時間內建立品牌地位。我們認為網路作為一個公共媒體,成熟後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即使會因此失去50%的流量,我們還是決定這麼做。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蕃薯藤在所有的入口網站裡面,研發能力可能是最強的,會讓我們在判斷上有空間,不急在一時。
就客觀的流量和業務量來看,好像也支持這樣的看法。如果不灌水的話,我相信我們的流量和網路廣告量還是第一,從去年十一月商業化後到今年六月,每個月廣告量都成長30%,現在都在賣明年夏天的廣告了。去年AC Nielson(收視閱聽率調查公司)的調查顯示,有57%的人最常使用蕃薯藤。
Q:蕃薯藤接下來的營運計畫是什麼?
A:未來兩三年還會是4C的概念,內容(Content)、通訊(Communication)、社群(Community)和電子商務(e-Commerce)。其實我們在去年轉型時,提出的不止四個C,還有一個不敢講的「大中華」(Chinese),因為蕃薯藤當時還是以台灣為主的網站,希望在今年底開始經營華人的大區域。網路沒有國界,要在網路裡生存,一定要有打亞運、奧運的準備,全國冠軍又怎樣?全國紀錄可不能比奧運入選標準還要低,那就沒得玩了。
Q:在蕃薯藤裡面,你怎麼樣讓人才匯聚並協力合作?
A:其實一個好的人才在挑公司時,在乎的是公司的品牌和名聲,特別是那些有工作經驗的人,我覺得正派經營是很關鍵的。第二個是公司制度和組織架構,再來是提供學習成長的機會,像我們的產品經理就有個讀書會,也鼓勵公司員工一起參加。網路變化太快,又很競爭,每個人的工作狀況都很滿載,假定沒有好的學習機制,員工很容易burn out。
Q:由於網路公司短期內都難有獲利的規劃,因此很多人都把上市當作台灣網際網路公司成功的指標,你的看法如何?
A:我們的布局是希望蕃薯藤成為產業轉型的重要團隊之一,我們如果想上市,是想募集資金,落實我們的business model,及更順利地推展業務,我們的想法是在明年下半年上市,不一定在NASDAQ上市,如果台灣有機會,我們還是希望留在台灣。現在看來機會愈來愈小,台灣的管理單位如果沒有意識到新的網路時代已經來臨,還是用製造業時代的老眼光去看,台灣公司最終只好等著被買。國界對這個行業沒有保護,隨時要面對第一流的競爭,台灣整個資金和人才的媒合做得這麼差,要怎麼和人家打?這不只是幾個business,這是一個新的industry!
Q:蕃薯藤的中國策略是什麼?
A:我們對中國的判斷,從來沒有樂觀與悲觀。我們的想法是:第一,要找當地的人合作。第二,我們要自己先去了解那個地方。我覺得大陸整個市場成熟時間會比較晚,不止在網路這一塊,主要是其他基礎建設的問題,例如金融和通訊。另外,有些在其他市場優先的東西,要擺到後面去,比如說內容,大陸你一下子去碰內容,可能會最快收起來,內容目前在大陸是管理比較嚴格,也比較保守的。
如果要整合亞太華人地區,那一定是台灣和大陸,台灣和大陸若能撇開政治的衝突,把雙方的know-how加在一起,可以把整合的時程壓到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