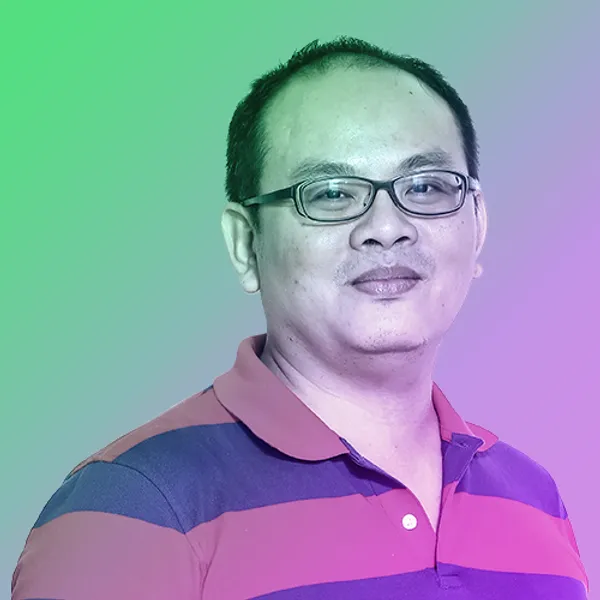「行きまーーす!(啟航了!)」就如同初代鋼彈駕駛阿姆羅出發前必定會喊出的口號,亞洲矽谷執行中心也在聖誕節這樣特殊的日子正式揭牌和啟航。
筆者也有幸受邀出席並且擔任下午場的物聯網論壇的主持人,所以既然都得來了,就乾脆一早來看看到底我們國家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多個媒體上已經有不少關於亞洲·矽谷揭牌的報導,我也就不再多做記錄,但我想談談我的一些觀察。
很多人會提到政府喜歡這種大堆頭式的開幕方式,還有象徵式的啟動儀式,我自己其實也是。但仔細想想,會這麼做的原因必然還是有民眾對這樣的方式買單,若公民不喜歡,透過持續的表達,政府終究是要滿足(娛樂)公民的,這種方式才會真的有機會慢慢改變。否則!這確實是政府告訴民眾「我們有做事」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揭牌和啟航儀式過後,現場的人潮走了一半,台上談市場趨勢的論壇場次其實很重要啊!怎麼副總統走了,這我還能理解,很容易有超多行程要走,但不是還有物聯網大聯盟嗎?怎麼相關的官員和人員好像都走了?
目前除了執行中心的關鍵七人小組現身之外,確實還沒有比較進一步和具體一點的作法,雖然在之前的熱烈討論中,社群許多人都在質疑為何這計畫必須在桃園?那段期間有許多討論,國發會這裡也重新檢討,沉寂了一陣子之後,隨著唐鳳政委上任,似乎畫龍點睛的加了個點(Dot)在亞洲矽谷中間,然後就順順的在桃園執行中心啟動了。
確實,執行中心在哪裡的問題不大,政府可以有其考量,只要讓積極想參與的民間社群理解政府執行的考量就好。而對桃園來說,爭取這個議題到桃園發展必然也能理解。所以,困難的是中央政府的論述得更清楚。
下午兩場的深度論壇以及座談,也就順著亞洲·矽谷的另一個重點,物聯網的議題。這也是我覺得有趣的,我們既然編組了物聯網大聯盟,也有物聯網志工團,但怎麼下午的物聯網論壇,除了必然在的執行中心團隊,物聯網大聯盟或者志工團似乎都不見了?
那麼我也就好奇物聯網大聯盟和志工團是用怎樣的機制方式來和社群以及其他人交流呢?
在啟動結束的不到一天,不少人都問了我看法,我必須說,由於政府執行的流程,所以一個創新的議題要在這樣的體制下進行本來就不容易。
我一直覺得應該強調公民素養,政府的所有作為到最後都必須滿足公民。
當我們在期待政府做創新的時候,是否又能接受創新的代價極大的機會像是打水漂?而看到政府打水漂,激不起太大的漣漪之後,我們是否會瞬間變成嚴格監督的酸民謾罵政府的監督不力?
如果會的話,那我們怎麼期待政府去做可能的創新和探索未來?
對於亞洲·矽谷,很多人在參加之後,感覺內容似乎有點空洞,或許是因為這跟最早提出的樣貌,在被媒體及社群批判一輪或者討論之後,似乎除了句點增加,實質的改變似乎不多有關。
實驗場域如何做到標準接軌?
如同在之前的文章談到的一些建議,我很樂意再次提起,其中我覺得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實驗場域,但卻也還沒能看到具體做法。政府要如何積極參與創新,提供可具體落地實驗的場域?不是什麼自造者空間(Maker Space),也不是什麼實驗室,而是實際測試的場域環境。
創建研發群聚是好的,但若最後依然只是大廠的舞台,那我先說這大概就輸了。積極的作法應該是:善用開放式創新的觀念、提供試驗場域,大廠和政府提供資源,讓新創用不一樣的角度做實驗,這樣才能同時達到實驗成本低、風險也低。
新創本就該冒險,而若大廠這樣都願意一起做,那就是真的想創新的大廠;而非只想用政府經費,協助降低自己研發費用而已。
物聯網產業大聯盟也絕對不要再像過去一樣,只是產業群聚的公協會,而是標準的接軌。
什麼是標準的接軌? 絕對不是成立那些線下聯盟或者協會,讓我們自己在島內自嗨; 而是能夠開放有競爭力的學者與企業有更多的合作,並且積極並直接參與國際標準協會,從參與跟隨,到建立影響力和發聲,這才是發揮我們實力和能力的場子。
有真正可以實驗的場域,和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作法,搭配願意投入早期的基金,或者是投資國外有價值的物聯網新創,透過場域的搭配,那麼就可以有很多有效的實質創新產生,進而帶動新產業生態的誕生。
不要被生態系的論述給綁住了!生態系是讓自己也成為其中可能的節點,融入然後發揮影響力,而不是建立我們自己的生態系,希望別人加入我們的生態系,這依然是「寧為雞首」的概念。
最後,曾經聽某個老前輩提到,政府投入資源資金的方式有時候會被既有的體制和系統卡住,要改變現況,確實需要長時間投入。但是至少要在資源資金到位後,執行時要搞對方向。才能用有效的方式滾動出實質效果,並且回頭導正體制。怎麼做?最會溝通的政府看來還得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