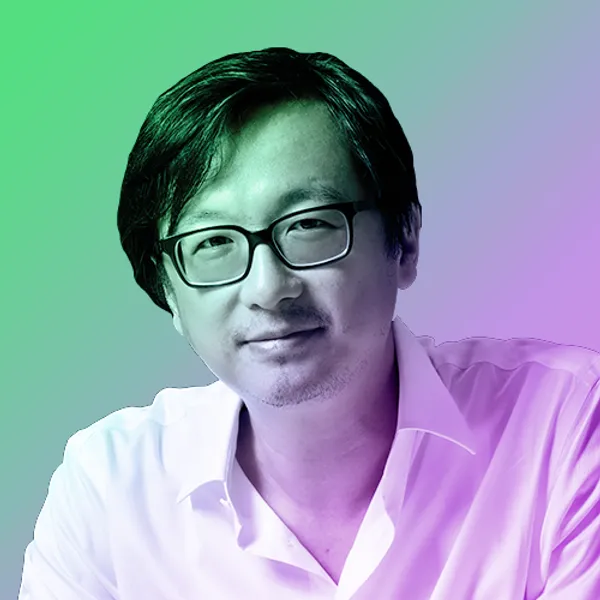在未來社會,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生或財富。一個美麗新世界……等等,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但前述的「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1958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英才制的崛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中,以反諷風格撰寫的情節,時間設定在未來2034年,「meritocracy」(英才制)一字首次出現。
註:「meritocracy」目前是通俗常用字眼,但中文翻譯沒有高度共識,此處翻譯稱「英才制」。
Michael Young所描述的未來,是他從19世紀後期逐漸展開的趨勢觀察而來,而在該文之後,那個未來已經成為我們的現實日常,「英才制」一字及其倡議的想法主導了世界: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英才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起跑點優勢、菁英驕傲,長期扭曲政經社會發展
回到2016年,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全球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歸咎於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鄉差距。以《正義》一書聞名全球公眾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今年秋天出版了《英才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書中指出這些現象是對「英才制」的反撲。
在前本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Sandel分析1980年代後,市場對自由的高度信仰,他認為這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機制,結果卻創造空洞而膚淺的公共論述,剝離公民對共同價值的討論;政治參與淪為「專家政治」,正好扣合英才制: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統治者。
註:50、60年代的重要思想著作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單向度的人》皆有過類似討論。
《英才的暴政》指出,雷根時期到歐巴馬時期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只要努力往上爬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2016年的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s)讓這個論述破產了。
Sandel認為,英才制其實是虛假幻想,成為菁英與否並非與財富無關。當代教育系統是社會流動重要機制,但美國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多來自富有家庭,他們有更多資源給小孩更好學習環境,再加上許多人脈關係。菁英學校的門檻有階級偏差,並非所有人都有真正公平的機會。
Sandel更指出,就算真是完美的英才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當階層化日益擴大,社會團結會被嚴重破壞。
另一方面,成功者往往以為自身的成功,是仰賴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成,而與社會無關,從而產生「英才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下層階級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並缺乏對於團體同胞的相互責任;最後,導致後者對贏家的憎恨,社會斷裂就或更嚴重。
於是,我們見到當前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如美國選民政治態度最概括化的分線——大學以上教育水準,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後者比較無知,故支持川普嗎?當然沒那麼簡單。
毋寧說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主導並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川普只是聰明地懂得去收割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表示:「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顛覆英才制,理想社會是什麼樣貌?
近幾年對英才制的抨擊已愈來愈猛烈。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Daniel Markovits的新書《英才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嚴厲批判英才制只是合理化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已經淪為自己原先反對的現象:「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與繼承機制」。
Sandel今年在《紐約時報》的投書指出,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人們開始更理解社會真正依賴的是誰,不只是醫生和護士重要,還有快遞員、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以及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其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沒有獲得最好的報酬、亦非獲得最多榮耀的人。」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其知識生涯正全然地對抗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英才的暴政》,他更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促進更平等的經濟政策,甚至建議透過「抽籤制度」來決定能否就讀菁英大學。
前述種種,或許都不是萬靈丹。
在《英才制的崛起》中,菁英統治最後結局,是一場反抗運動導致菁英的垮台——不正是2016年真實上演的情節?
Young的寫作初衷,是為了避免菁英政治走到這步田地。他對美好世界的提醒是:「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度,以及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以此,每個人都將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獨特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而非在任何數字構成的準則爬上爬下。」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本文出自數位時代318期11月號《台灣下一個世界級產業:智慧醫療》 《專家觀點》
責任編輯:張庭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