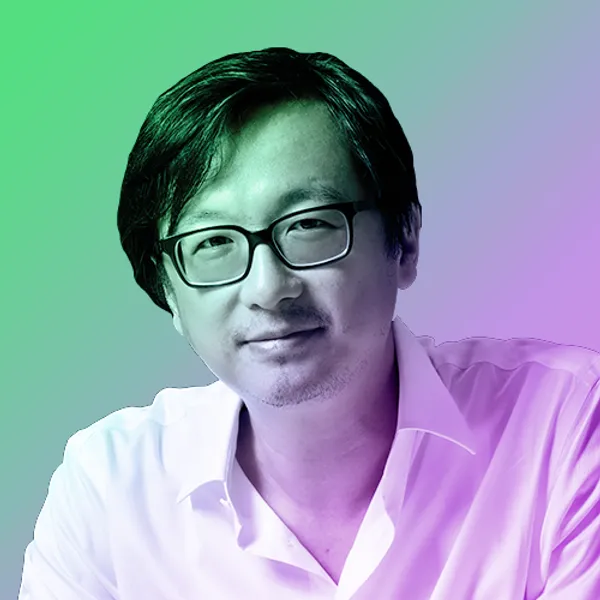2015年,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法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他本來想要警告畢業生,未來不要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來謀取個人利益,要積極地為公眾利益服務。但他在寫稿時突然了解到,這群天之驕子所承繼的特權在為他們提供競爭優勢的同時,也為他們帶來磨難。
他在演講台上跟學生說:「你們的生命被毀了。」他說,你們的一生不斷地努力學習、工作,而未來必須繼續如此,如此才能維持你和你小孩在菁英階級中的位置,維持你的菁英性。你必須一直拚下去,「把自己用盡。」
然後,這位教授寫了一本書《英才制的陷阱》(The Trap of meritocracy,2019年出版。中譯本名為「菁英體制的陷阱」)。
教育固化菁英階層,養成優越的「現代貴族」
對英才制的批判在這幾年是熱門議題,而且評論者就是來自這些菁英中的菁英學府。丹尼爾・馬科維茨是耶魯的法學博士(J.D.)、牛津的哲學博士,碩士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計量經濟學,大學是耶魯大學數學學位。此前我也在這裡的專欄討論過哈佛大學知名政治哲學家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成功的反思》。
在歷史上,先是世襲貴族統治世界,然後是土地和資本的掌握者成為統治者。到了20世紀中期,美國的幾個主要菁英大學開放大門,讓更多成績優異的小孩得以進入窄門,菁英教育性質於是改變,企業也有了更多高級菁英可以用,「英才制」開始主導世界。
這看似是很大的進步:人人機會平等,可以透過好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再是看血統與非自己掌握的因素。
但「英才制是虛假的」,馬科維茨說。如今的世界是一種「英才的不平等」,這些最頂尖才能、最努力的和得到最好教育的人(尤其集中在科技、金融、醫學和法律領域),獲得極高的報酬、聲望與權力,成為這個世界的新菁英。「英才制造成一種前所未見且獨樹一格的失衡情況,使得新鍍金時代大為失色。菁英們不僅是壟斷了所得、財富與權勢,同時也把持了產業、公共榮譽與個人尊嚴。菁英體制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社經利益之外,同時還號召菁英們集體進行一場維護其階層的毀滅性競賽。」
他認為這個菁英階層已經鞏固起一套新時代的世襲制:他們從小就花更多資源培養小孩,讓他們更聰明、更有競爭力,更能進入最好的學校。如此代代相傳,教育體制只是不斷再生產與深化社會既有的不平等。
而且這個現代貴族階層,如同古早時代,在每一方面都是和其他人區隔開來:從就讀學校、消費方式、通婚對象,和居住區域。至少在美國,這是一個全面分裂的世界。「這些差異不斷累積,最終導致菁英體制造成的分裂過於巨大、難以聯繫,富人與一般大眾不相往來,相互之間也沒有同理心與同情心。」
停止報酬不均,才能避免撕裂加劇
但情況並非一直都如此。二戰後初期美國社會相對平等,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富裕社會。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當年家庭背景大不相同,但他們的生活和機遇並沒有差異很大。
英才制,原本應該是讓世界變得更公平,現在卻變成其原本所要對抗的一切:一個集中財富與特權的新階級,而且是可以延續幾個世代的現代種姓制度。
《英才制的陷阱》最獨特、也許最爭議的觀點是:一如本文開頭的演講,馬科維茨不是要批評這些菁英做錯了什麼,而是指出他們也是自我剝削的受害者。
「菁英工作場所,例如科技業、銀行、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甚至一些大型企業與其他的『白領鹽礦坑(意謂極端辛苦與壓迫的工作場所)』並無二致。」菁英的工作場所令人耗盡心力,而他們會發現自己愈來愈難從他們的工作中找到熱情與意義。
舊時代下的傳統財富較能夠允許貴族階層表現自我,新財富卻是使得菁英失去自我。「菁英體制為菁英階層帶來心靈上的痛苦,使他們陷入存在性焦慮與深沉的異化之中,即使是再多的所得與再高的地位,都無法減輕這樣的痛苦。」
但真的大多數超級菁英都真的這麼痛苦嗎?馬科維茨或許同情他的學生(和自己),但這個對他們痛苦的同情,看在不屬於那一小撮人的大眾中,可能會不是滋味。
真正問題的核心,不是在於拒絕讓有才能、有努力的人更多回報,而是所謂英才的菁英應該更多元化,不該只是少數產業頂層的報酬、和社會其他人距離如此天差地遠。
正如知名倫理學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言,我們需要承認人類有不同天份。「所以唯有能給予這些不具有最高薪資工作的才能的人適當報酬——事實上這些工作可能對我們社會是更必要的,從教師、護士、警察到清潔人員——英才制才是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理想。」
責任編輯:林佳葦、張庭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