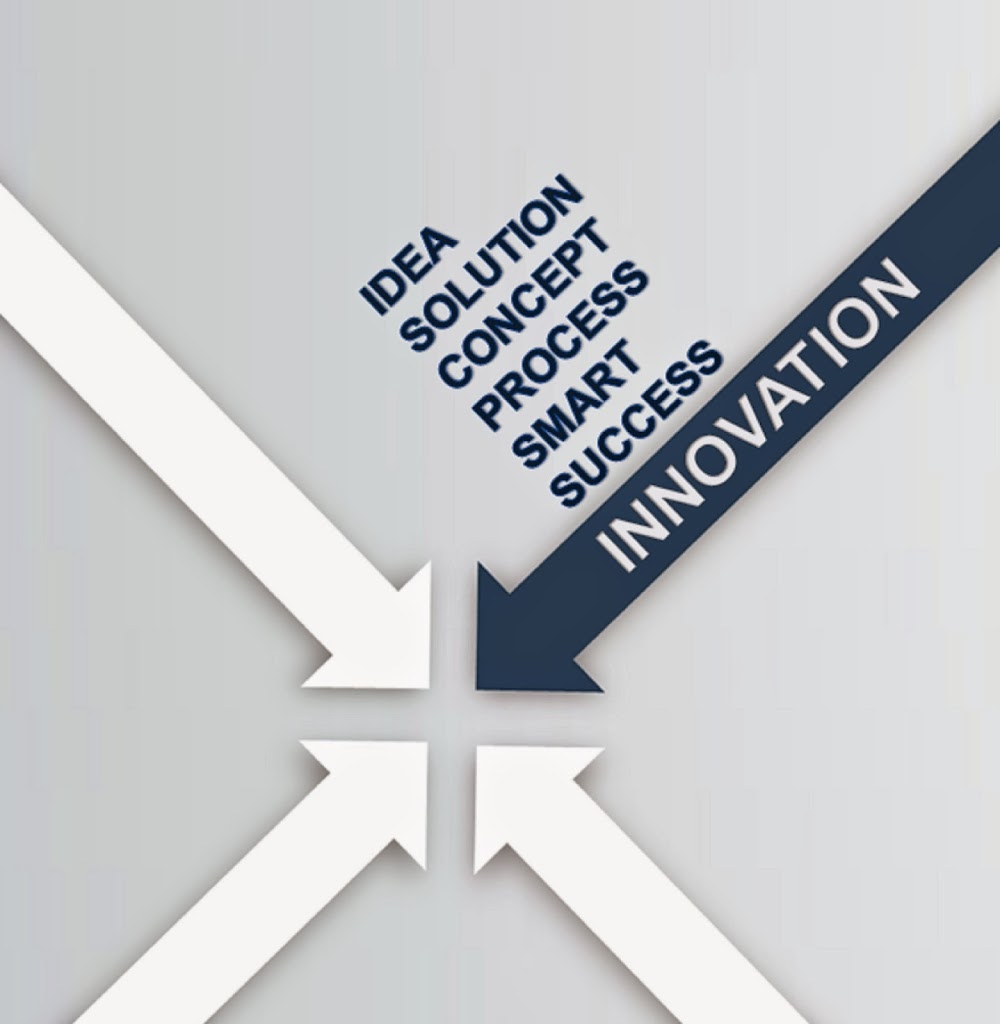「接班人問題」是世界頂尖企業董事會每年都要討論的問題。像奇異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選定接班人伊爾梅特(Jeffrey Immelt),前後共花費三十六年心血;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交棒給鮑爾默(Steve Ballmer)也經歷了數年考驗。對美國董事會來說,「接班人計畫」已經成為第二重要的議題,僅次於領導者是否適任。
包括英特爾(Intel)、杜邦(Dupont)、可口可樂(Coca-Cola)、沃爾瑪百貨(Wal-Mart)、索尼(Sony)、惠普(HP)等這些一流企業能夠縱橫商界近百年而不墜,靠的就是一棒一棒的接力,反觀台灣第一大民營製造公司鴻海科技集團的交棒工程,則一直被外界視為最大的弱點。
「別人愈不相信的事,我愈會去做!」郭台銘面對外界對於科技強人交棒難的質疑,曾一再表示會把棒子趕快交出去,但是眼看二○○八年已經進入倒數,但是外界仍舊悲觀,誠如政大教授司徒達賢公開直言:「台灣成功的創業家本身也缺乏接班經驗!」
**台塑模式
由資深幹部共組決策小組
**
專業經理人交棒給專業經理人,都需要很高的管理技巧,更何況沒有經驗的創業家交棒。司徒達賢就指出,對台灣企業來說,交棒困難,還包括了以下三點:一是創業家有觀照全局的思考能力,本身太能幹,而不放心把畢生心血交給別人;二是在自己公司之中,若自己不提出這個議題,別人更不好意思表示意見;三是由於台灣的公司治理沒有上軌道,如果把經營權交到「外人」手上,被「整碗捧去」的風險很高。
這也難怪「接班話題」在台灣企業界一直是個隱形的命題,在實際的情況之下面臨了很多困難。但是儘管如此,二○○六年的六月五日,台塑集團仍宣布世紀交班,八十九歲的董事長王永慶和八十五歲的王永在宣布卸下權力,交由子女和專業經理人組成的「七人決策小組」負責策略和營運,這七人決策小組仍有執行長一職,交由五十九歲的王文淵掌舵,讓台塑領導人一夕之間年輕三十歲。
採「七人決策小組」共同領導,顯然是台塑準備「長壽」的方式,這會成為鴻海的學習方式嗎?如果鴻海要成立「決策小組」,各大事業群總經理及財務長黃秋蓮、會計長李金明、技術長陳杰良等一定是重要決策成員,其中最資深的幹部包括戴正吳、盧松青、黃秋蓮等超過十五年以上資歷者,由於人脈深厚,就有可能在這種模式之下成為決策小組的「接班人」。
**台積電模式
郭董指定接班再從旁協助
**
但是科技產業變化快速,充滿風險,用「共識決」來做決策,很容易延誤商機,共高盛證券分析師金文衡則認為,鴻海未來比較有機會走的是「台積電模式」。
金文衡認為在二○○六年股東會上郭台銘也講得非常清楚,兩年之後他是要交出CEO(總裁)的位子,但還會繼續擔任「董事長」。而且接下來,他也會繼續以教練的角度,來協助他的接班人(或者團隊),所以說,他對鴻海的掌握度與影響力,並不會受到影響。
最近郭台銘也漸漸不去干涉每個事業群主管的例行事務,授權的程度也愈來愈高。這樣的做法比較像張忠謀把CEO位子交給蔡力行,然後逐漸淡出台積電,現在張忠謀已漸漸變成台積電的精神領袖,其實,郭台銘也說,未來他也只想當鴻海的精神象徵而已。
而外界質疑,如果郭台銘交棒之後,接班人管得住所有經理人嗎?金文衡認為,目前鴻海的內部各個事業群,都是一座座山頭,在郭台銘的領導之下,最後的決定權與裁決者還是他,就算各個山頭有任何問題,還是會被壓住的。而他之所以要在兩年後先交出CEO,也是為了培養接班人的威望,因此,在未來五年內這個問題應該不會發生,至於郭台銘卸下董事長之後,會不會發生就很難評估了。
在台積電模式之下,盧松青的美式背景及個人戰功,就成為接手營運,成為下一任執行長的有利條件。事實上「台積電模式」其實就是「英特爾模式」。從英特爾創辦人之一的高登摩爾(Gordon Moore)交棒執行長給安迪葛洛夫(Andrew S. Grove),摩爾則擔任董事長,到葛洛夫交棒給貝瑞特(Craig Barrett),自己也先擔任董事長,最後貝瑞特交棒給歐特寧(Paul Otellini),自己也接董事長,都是為了讓年輕接班人能夠上手,又能兼顧風險的平衡。
從貝瑞特到歐特寧,都是在營運長時代就已被指名接班,但是這種提前先曝光的指名一人做法,真的適用於東方企業嗎?郭台銘就曾指出,接班人一旦曝光,就會成為群起攻之的對象,這或許是他一次宣布九(十?)大事業群總經理,人人都是「接班梯隊」的用心所在。
《執行力》一書共同作者瑞姆.夏藍(Ram.Charan)在《哈佛商業評論》點出,隨著企業競爭環境激烈,接任執行長最佳年紀為四十六到五十二歲,原因是這時處於顛峰,而且上任後可以有至少十年的作為。傑克.威爾許接掌奇異(GE)執行長時,也不過四十五歲。瑞姆.夏藍的研究,準接班人可以循序漸進掌管愈來愈大且複雜的利潤中心。目的是要有機會負責單位「盈虧」。這些其實也和郭台銘在推動的接班工程不謀而合,讓各事業群總經理自負盈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有掌握爆發性的產品和市場,在九(十?)大事業群中四十五歲以下的總經理,包括簡宜彬、蔣浩良、鍾少文等,也有後發先至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年輕人的出頭而不被資深幹部排斥,加上鴻海太大,還是要靠有計畫的栽培。
**鄧小平模式
集體領導讓權力不被寡占
**要讓龐大的版圖能夠和平轉手,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則做了一種示範。鄧小平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意識到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就推不動經濟體制改革,因為首先一定會遇到「人」的障礙,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更建立起一套權力轉移的遊戲規則,亦即「集體領導」與「梯隊接班」的制度。
「集體領導」制度也在避免中共在歷代權力遞轉的時期,無論是「毛澤東V.S.林彪」、「華國鋒V.S.鄧小平」的激烈政治鬥爭。鄧在掌權期間,就橫跨了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政權交接的歷程,鄧小平在人事操盤上卻是有計畫地以「年齡」作為接班的依據:中央、省與其同級之幹部,正職不超過六十五歲,副職不超過六十歲,司局長一級幹部以六十歲為限,梯隊接班機制的目的,是透過有計畫選拔、磨練中生代幹部,使得權力核心成員的年齡呈現多層次以上的分布。
年輕幹部在「傳」、「幫」、「帶」的情形下逐漸接掌權力,而鄧小平為打破黨內對毛澤東的個人迷思,更強調「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集體決定了事情,就要分頭去辦,各負其責!」鄧小平如此要求。而他所建立的「集體領導」與「梯隊接班」的遊戲規則經過了三屆黨代表大會的運作後,漸次成為「權力轉移」與「權力核心」確立的主要依據。
鄧小平之所以這樣設計,主要是希望在「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兩大框架下,形成了「個人」無法獨力掌握整個政權的局面,也讓年輕人可以在隔代接班,但商業畢竟不是政治,在迅速變化的市場上,挑戰從四面八方而來,鴻海雖然大如一架超級航空母艦,卻也更需要快速變化的戰鬥隊型。
**倒金字塔模式
讓年輕基層成為決策主力
**「鴻海內部正從過去金字塔型的組織,走向一個倒金字塔結構,來準備應付外界挑戰!」鴻海連接器事業群總經理游象富說,從業務的觀點來看,以前誰最能接到客戶?是老闆對老闆比較容易;但是產品的多元化及市場快速變化,現在反而是基層最能接觸到客戶,也就是金字塔的「基部」才是主力。
其實不只是董事長郭台銘,游象富指出,連他們這些資深的幹部都要開始往後退,讓過去金字塔朝上的「尖部」變成領導統御的基石,游象富進一步闡述郭台銘對於「領導統御」的看法:「領」就是方向,「導」就是老師,「統」就是整合,「御」就是管理,而責任及決策盡量讓年輕人去承擔,「不要讓層峰,變成層『瘋』啦!」游象富笑說。
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尾牙舞台的正面出場處貼著一幅門聯,左聯「爭權奪利是好漢」,右聯是「開疆闢土真英雄」,橫批則是「出將入相」,主要就是激勵新生代幹部早日接班,一定可以「出將如相」,讓人才出頭,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從二○○七年最大的變化,就是鴻海在推動年輕化,而鴻海的「接班工程」就是推動集團的年輕化。
美國《財星》雜誌在二○○一年時統計美國前一百大企業,年紀超過六十歲的執行長成為「少數民族」,只剩四分之一,也難怪明年五十八歲的郭台銘積極退休,而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統計,缺乏完善的接班制度,有五分之二新任執行長會在一年半內陣亡,所以郭台銘要完成接班大計,最重要的挑戰,還是和時間賽跑。
像奇異公司選擇接班人的做法,是投入大量的時間了解幾位競爭者,同時,花更多的時間討論繼任人的最佳方案,這些方案,一般公司需要董事投入的時間超不過一百個小時,而奇異的董事會卻花了幾千個小時。
從二○○七年初到○八年初,郭台銘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超過一萬個小時可以運用,來籌劃接班大計,而這也是鴻海從三十年企業邁向百年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