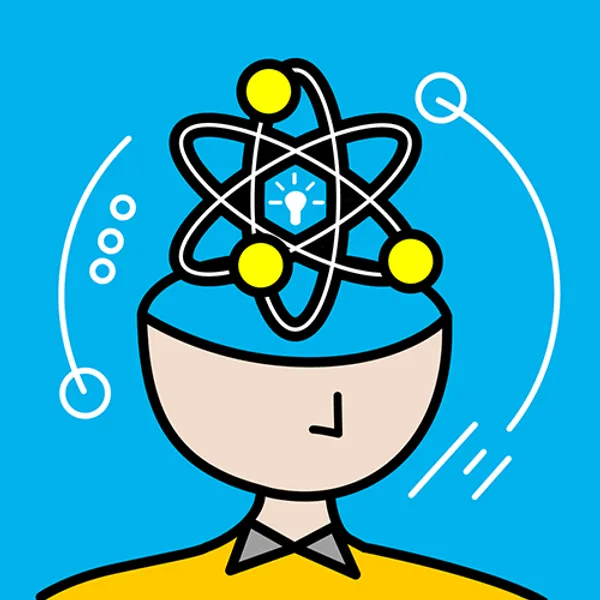我的青春恰逢冷戰年代的尾聲,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還曾因八十年代試圖與「自由中國」寫信聯絡的舊事,而遭遇沒完沒了的盤問、審查及封殺。
2007年末,我受臺灣數位文化協會(ADCT)之邀,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其間的五味雜陳自然溢於言表。
此行緣於推特。
那時候,推特開張一年多,我使用它也不過半年,同時做著一個播客(Podcast)「反波」。
反波在對岸也引起了小範圍關注,推特上已經相互follow的史萊姆是臺灣數位文化協會的。有一天他問我和我的播客搭檔飛豬,有沒有興趣到臺灣參加一個與互聯網有關的活動。我當然做夢都想去臺灣,可怎麼去啊。那時候,大陸還沒開通臺灣自由行。
推特上的大陸推友毛向輝給我們出了個好主意——用港澳通行證到香港,只要有臺灣方面的邀請函,並拿到入台證,那麼你盡可以在香港消失,前往臺灣,不留任何痕跡。而且,毛向輝已經用這種辦法去過好幾次臺灣了,完全沒問題。
就這麼著,我和飛豬終於肉身翻牆,成功「偷渡」臺灣。當時,還是陳水扁執政,整個臺北籠罩在入聯公投的氣氛中。兩岸關係也因此處於緊繃時段。
更重要的,大陸人民還能夠自由登陸推特。我這個半年多的推特中文用戶,理所當然收穫了一批臺灣推友。
生平第一次臺灣之行,也就變成了推友聚會。我和飛豬臨行前特別買了一些北京出產的風箏之類的小玩意。
於是,見到了「活的」臺灣推友——工頭堅、凱洛、張鐵志、阿吱、長官、Fred、豬小草、卡謬佬、阿西摩、大師兄、Vista、686、陸君、浩、奶爸、小海……
至今印象深刻的畫面有幾則:在「喫飯」門口,午後,我們這些推友低空放起了我們帶去的風箏,一位女推友特地跑出去老遠給我和飛豬買來了好喝的臺灣飲品;我對台共很感興趣,一位推友的長輩曾是台共,某個晚上,他和我講了長輩悲喜與幻滅;一眾推友力薦我們去參觀「臺灣人權景美園區」,體驗「戒嚴時期」的陰森恐怖……
當年的推特中文圈,至少在我的Timeline上顯現的,有它獨有的互聯網社交模式,大家在推特上互相follow,政治觀點上互相接納,生活方式上互通有無,從晨起一餐到藍綠身份,差異與不同造就了多元、成就了視野。
這種互聯網社交方式,與微博或微信大不相同。微博火藥味弄些,微信秀場色彩多些。
或者,當年的推特中文圈,也是綻放的曇花?
那次因推特成行的臺灣之旅,當然也是第一次體驗臺灣之日常。之前有過在「滾石唱片」北京辦公室的工作經歷,不乏與臺灣人接觸,但在臺灣的土地上,和在推特上已經頗為熟悉的推友,或大快朵頤,或直抒胸臆,冷戰氣息漸次消退,逐漸被溫暖熱情包圍。
回京之後,我和飛豬把一路拍的照片做成了明信片,寄給了臺灣推友作為紀念。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大陸終於封鎖了推特,翻牆的麻煩造成了上推熱情的減退。但當年的推友,有些終於成了「落地」的朋友,史萊姆更是拉著我的另一位臺灣推友Qweaz到上海打拼事業,如今已是風生水起。
我後來再去臺灣,甚至住到了Qweaz在淡水的家,他人在上海,我拿著他家的鑰匙,假裝自己就是淡水人,吃個早飯,散步到推友686開的有河Book。我也還是偶爾翻牆,去看看在旅遊業大展身手的工頭堅又到了哪個國家。他和美麗的凱洛小姐幾年前終於修成正果,走進婚姻殿堂。第二次在台期間,當年的推友Candice已經搬到南部,邀請我去玩,但終因行程原因未能成行,非常遺憾。至於張鐵志,我們交集較多,他小住香港期間,我在廣州,我去香港,我們還不時約在一起聊聊時局,歎歎氣。
我不相信緣分,但有時候世間的奇妙確實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在今年春節前不久,經推友阿吱介紹,因為工作上的原因,在上海與臺灣中子文化的人開會,一見面,其中一位朋友說:「平客,我們是當年的推友。」說話的是推特上的陸君,我們可能會在接下來的時間有共事的機會。這是推友變戰友嗎?
推特被牆之後,我也有上推非常頻繁的時期,比如「太陽花學運」。我覺得,到了「太陽花」時期,中文推特圈已經大不同。但我還是樂於把我變身為在地的臺灣人,換個角度看那些訴求。
那些時刻,我會暗自想,地球上說華文的人居住的版圖,幸好還有臺灣。
十年推特,周遭已是物是人非。大有「山河依舊、故人何在」的慨歎。推特還是那隻自由的小鳥,它的鳴叫首先讓我和對岸開始了不可能的溝通交流。十年間,我這個就要成為老古董的人,經常慨歎,當年給對岸寫封信,居然都被封殺(更早是坐牢),而現在,我們竟然可以「那麼遠、這麼近」。
人到中年,哪裡是下午茶,明明是隔夜茶。也因此經常想這世間的千奇百怪究竟為何。人類怎麼就在二十世紀下半頁,有了那荒唐的幾十年?一些瘋子用美麗的血腥謊言砌了一堵堵牆,有人為了翻牆,家破人亡,一命嗚呼,甚至就在牆就要被推倒的前夜。
我終究是幸運的,沒有為與自由對話的渴望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
而我堅信,就算美麗的血腥謊言揮之不去,但所有牆,最終都是要被推翻的。
(平客,推特帳號 @buchimifan,媒體人,現居北京)
(附上當年做的推友明信片,攝影/飛豬)